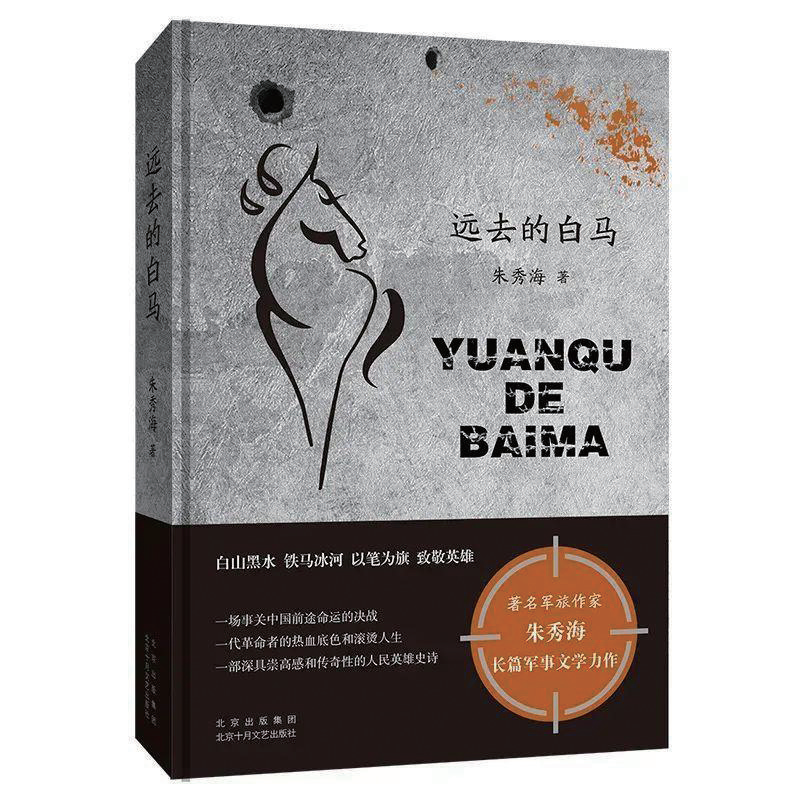
在我的文學生涯中,長篇小說《遠去的白馬》(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)創(chuàng)作過程不是最艱難的,卻是時間跨度最長的。2003年初夏,為了撰寫一部人物傳記,我開啟了一段實地采訪。本來因為手頭還有《喬家大院》的劇本創(chuàng)作任務,我希望采訪能盡快結束。但很快便發(fā)現(xiàn),這是不可能的,因為我已經(jīng)走進了解放戰(zhàn)爭中一段波瀾壯闊的血與火淬煉的歷史。
在隨后的13個月里,我行走11個省區(qū)市,采訪130多位歷史見證人,一次次被其中的人和事所震撼。2008年,我結束了傳記寫作工作,但對那個在解放戰(zhàn)爭中建立功勛的英雄團隊(書中的37團)的關注沒有結束,對本書女主角趙秀英和37團其他英雄事跡追蹤沒有終止,一直延伸到2019年夏季。
那是一個雨天下午,我接到了一個電話。打電話來的是那次采訪中結識的一位老英雄的后代,他告訴我,他的父親在當年春天過世了。掛斷電話,我憶起了老英雄生前騎著白馬馳騁于東北風雪戰(zhàn)場的情景,驀然間悲傷和急迫感襲上心頭,敦促我把這個一直想寫、一直在醞釀,卻一直不敢貿(mào)然動筆的英雄團寫出來,把那些為新中國做出貢獻的人民英雄的事跡和精神寫出來,不讓其隨著一代人的離去而被埋沒和遺忘。
《遠去的白馬》講述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: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,我膠東地區(qū)數(shù)萬部隊緊急渡海,參加解放東北的戰(zhàn)斗。共產(chǎn)黨員、區(qū)支前隊隊長趙秀英,在登陸東北后,為了找回失散的支前隊隊員,完成她對支前家屬的承諾,毅然留在臨時組建的37團,與全團官兵一起出生入死。她親眼見證37團面對新的戰(zhàn)場環(huán)境和戰(zhàn)爭態(tài)勢,怎樣克服重重困難,拼出一條生路,并且在戰(zhàn)爭中逐漸成長、成熟,經(jīng)過堅守摩天嶺、四保臨江、突襲通化、塔山阻擊等驚心動魄的浴血奮戰(zhàn)后,最終成為一支經(jīng)得起嚴酷戰(zhàn)爭考驗的勁旅。大軍入關并打完平津戰(zhàn)役后,趙秀英回到山東,隱去功與名,從膠東老家搬進沂蒙深山,把戰(zhàn)爭歲月的記憶埋在心中,任勞任怨地度過一生。
這部書從采訪到寫作,中間跨越了16年。16年的追蹤和想念,這些英雄人物及其故事在我心里埋藏了多久,壓抑了多久,等到寫作時,他們像隊伍一樣沖鋒、像江河一樣奔涌的氣勢和力量就有多強大?!哆h去的白馬》的創(chuàng)作歷程讓我明白真實是創(chuàng)作者最強大的武器。有了對真實歷史的了解,才會有真正的感動和創(chuàng)作的熱情。當初是真實的歷史、真實的歷史人物、歷史人物真實的英雄心深深地打動了我,今天經(jīng)由我的筆,他們也同樣感動了不少讀到這部書的朋友。文學的力量正在于這種感動的傳遞。
我知道,在書寫紅色革命歷史的文學長河中,《遠去的白馬》只是一朵浪花。類似37團這樣頑強戰(zhàn)斗的英雄團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里比比皆是,像趙秀英那樣毅然投身革命、一生奉獻人民的感人形象在革命歷史中也為數(shù)眾多。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,其原因不但在于他們當年的浴血奮戰(zhàn)、英勇犧牲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,更在于他們的理想、他們的信仰、他們毅然堅守并為之奮斗終生的價值,和我們今天的時代血肉相連。他們的事跡和精神值得我們一再回眸、鄭重記取。
無論是趙秀英大姐,還是37團的英雄們,在他們所處的那個年代,都只是最普通的中國人。他們本是生于窮鄉(xiāng)僻壤的農(nóng)民,懷著對革命樸素和真誠的理解,投身于推翻舊中國、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戰(zhàn)斗,成了中華民族歷來歌頌的“捐軀赴國難,誓死忽如歸”的英雄。在決定民族命運的時刻,人民顯示出他們的品格和力量。
《遠去的白馬》是我對前輩英雄的致敬。作為一名軍人,我永遠堅定地相信:力量在人民之中,英雄在人民之中。烽火洗禮的老一輩英雄雖然漸次遠去,但是他們的功業(yè)、精神、風骨會和我們的民族一起萬古長存,鼓舞后人披荊斬棘、走向未來。



